作为一种文学研究方法的数字人文 ——印刷文化基础设施,20世纪文学批评史,以及文学社会学
作者:姜文涛;转自:公众号 DH数字人文
本文原载《中国比较文学》2019年第4期,此为作者提供原始手稿。
———————————–
摘要:数字人文文学研究成为一种在迅速发展的文学研究方法。本文以长时段历史视野讨论“晚期人文批评”时代这一种人文学批评方法的可能性。人文学科是随着近代印刷文化的兴起而历史地产生的知识机构化形式;无论是在新批评时代、还是在批评理论盛行的时代,文学研究批评者始终带有精英主义“教导者”的角色色彩;计算和统计的方法在文学研究中一直存在,是其近代科学化进程的一个侧面。从文学研究作为近代学科体制的建立、到数字人文作为一种方法,人文知识不断地被机构化生产和流传,是知识民主化的进程,批评者的角色不断地被赋予不同的职业形象和技能特征。本文提议重视文献文本基础设施、重视中国文学研究历史和传统的数字人文文学研究。
关键词:数字人文文学研究;印刷文化基础设施;统计方法;计量分析;晚期人文批评
Abstract: Digital humanities has been a rising method for literary studies. This essay discusses the possibilities this method would bring to literary studies in the so-called late humanities critique, with a perspective of the discipline of literary studies in the historical longue durée. Humanities studies in university settings are disciplined forms of knowledge that came into being with the rise of modern print culture. The role of literary critic has sustained for itself an intensively ascetic-pedagogical dimension in the era of New Criticism as well as in the era of Theory. Computational and statistical methods are manifestations of the scientific dimensions in literary studies. From the beginning of literary studies as a disciplinary form of knowledge to digital humanities as one of the methods, humanities knowledge has been constantly institutionalized and disseminated, the process of which is that of democraticizing knowledge. The professional role of literary critic has been identified with various images and expertise. This essay proposes a digital humanities method in literary studies modeled on the foundational technology of textual scholarship and on the scholarly immersion in the history and tradi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studies.
Keywords: Digital Humanities Literary Studies; print culture infrastructure; statistical methods; computational analysis; late humanities critique————————————————————–
一、印刷文化基础设施与近代文学研究
我们身处数字时代,数据信息非常丰富。技术物质条件的变化必然要求产生新的人文社会研究方法、新的知识论和新的知识生产主体。数字技术媒体环境的到来,必然会影响到由印刷时代以来形成的知识生产机制和大学学科体制。而后者的形成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弗吉尼亚大学查德·魏尓蒙(Chad Wellmon)教授的研究表明,在19世纪前半期的西欧,作为近代印刷文化兴起的一个结果,文学研究开始成为大学中人文学科知识生产体制的一部分。比如,奥古斯特·威廉·冯·施莱格尔(August Wilhelm Schlegel, 1767-1845)将“纯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写作范畴、一种从大量的印刷文本中过滤和挑选出来的写作。在施莱格尔看来,文学不仅仅是“粗糙的书本堆积,”而是对某种“精神”的显明表达,对某种共同生活状态的表达。正是这种共同的民族精神赋予文学整体性,使之成为“作为一个系统性的、完备自足的作品集合”(Wellmon 78)。英国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见证了一个由印刷文化的发展带来的阅读和写作引起的人们的日常生活秩序感不断发生变化的世界。在这个历史时期内,近代意义上的阅读大众和社会阶层开始出现,诞生了不同阶层的阅读大众,这使得当时的浪漫主义作家纷纷采取不同的策略意图去形塑具有不同阐释模式和意识形态框架的阅读大众。这个历史时期内,近代意义上的阅读大众和社会阶层开始出现。
从词源上来看,“文学”这个英文词汇一方面指的是“学识或知识修养,”另一方面指近代意义上的某些写作文类之内的、文学研究范围包括的书写形式和题材。纽约大学克里夫·希斯金教授(Clifford Siskin)和加州大学威廉·沃纳教授(William Warner)认为,这个词这种双重语义的历史性出现是近代印刷文化媒体技术革命引发的,与近代大学人文知识的产生密切相关(Warner and Siskin 104)。事实上,苏格兰的一些大学早在18世纪就开设了英语文学方面的课程。比如,被后世称为政治经济学家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于1748-1751年间就在爱丁堡大学主讲英国文学和修辞。按照希斯金教授的研究,17世纪晚期报纸开始推广,18世纪早期出现了各种杂志,可以认为在18世纪的转折点书写在形式、内容和所产生的社会语境方面皆出现了具有近代化特征的转向。这种转向逐步地发生发展,随着技术和经济等一系列社会因素的综合性作用,1830年出现了一种分水岭式的变化。他认为,在这之前,书写的整个流程(从写作的产生到阅读的过程)得以在一个具有等级秩序的有关知识和劳作的体系里面完成了其规范化和理性化。也即是说,有关书写的近代学科性和职业化进程在1830年代来临之前得以完成。这是英语文学,即英国的国别文学,开始成为“英语系”学科知识生产对象的历史时期。在希斯金教授看来,这个“学科性的路径”是这样的:它生产了“一种形式的书写,这种书写实验性地将自身及其它类型的书写组织进有关‘深刻’知识的叙事之中”(Siskin 11-12, 135)。就是在这样的历史社会语境中,文学、文学批评和审美等人文学科的教育成为知识生产的范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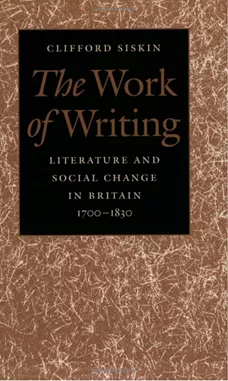
二、新批评派细读和政治解读
作为一种文学研究的方法,新批评运动起自于20世纪初,至20世纪五十年代盛行于北美文学研究和大学教育中,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在现代大学体制的背景下对于文学研究方法论的反思和提倡。其典型的分析方法为“细读。”这种方法带来的是文学批评的职业化:批评者从单个的文本之中提取出作品的意义、甚至是作者的意图,作者创作作品的美学价值经过批评者的劳作、成为读者可以从中享受到快感的知识。其创建型人物包括I.A.瑞恰慈(I. A. Richards)和F.R.利维斯(F. R. Leavis)。在英国,他们在1932年创建了一个作为理论宣传阵地的刊物《细察》(Scrutiny)。这份刊物运行了22年,刊物上除了偶尔发表关于政治和教育的文章之外,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对英语文学的再评价。在其最受欢迎的20世纪五十年代,曾印刷发行1500多份,这其中绝大多数订户来自于英美大学和学院研究机构的图书馆。这似乎也说明了新批评的方法至少部分地是事关大学学科体制化了的文学知识生产。在其刊发的九百多篇文章中,F.R.利维斯和他的妻子Q.D.利维斯发表的文章多达两百多篇。这使得这份杂志也体现了他们作为文学批评者的独特的个人主义色彩。
利维斯将多数发表在《细察》上的文章放入其著作《伟大的传统》之中。这本著作的标题本身就说明了这是一次关于英国小说经典的发现和整理。在其中,利维斯认为:“那些堪与在诗人相比相埒的重要小说家——他们不仅为同行和读者改变了艺术的潜能,而且就其所促发的人性意识——对于生活潜能的意识而言, 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利维斯很关注作家们对于人性和社会生活方面的道德判断。利维斯认为:“处于我们文化中心的是语言,它承载着我们的精神传统、道德传统和情感传统,”“假如语言在当代的使用趋于贬值,而非促其焕发出生活活力,那么我们只有寄希望于文学,只有文学保持了语言最精微、最美妙的使用,与我们的精神传统相连,记录着‘人类对过去的最佳体验’”(张瑞卿 206)。在利维斯看来,文学批评者的职责是从文学作品之中寻找一个民族的“精神传统、道德传统和情感传统” (张瑞卿 206),这让人想到了前文所引的施莱格尔关于“纯文学”的浪漫主义式的理论化,一方面提升了批评家的地位,批评家的作用不再是在作家之后的第二位的;另一方面,这样的身份地位使得批评家必然会去努力建立一个本民族本文化的文学经典了。
美国新批评的发展同样强调文学的美学和伦理学层面。比如,其主要理论家柯林斯·布鲁克斯(Cleans Brooks)在他的《精致的瓮》一书中认为,诗歌的形式是一个“精致的瓮”,“瓮是一个有形式的物体,一个自足的世界”,这为如何“整体性”地阅读一首诗提供了一个样式;“一首诗所有的诗行,整首诗,这些作为一个诗学结构”。对他来说,“诗人[……]必须使我们恢复经验的整全性,就如人们好像在经历中知道的那般:”诗人提供给我们一种“洞察力,让我们存有经验的整全性,它在最高最为严肃的层面上将经验之中表面上互为冲突矛盾的因素统一为一个新的模式”。他又认为,诗歌的结构像戏剧,体现了一个将互相冲突的因素放在一起的动态的过程(Brooks 149, 152, 112, 186-187)。这样的文学观念将文学置于与人类经验同等重要的位置,认为阅读一首诗或者一本小说提供了阐释人类复杂经验的机会,课堂之中的阅读和文本阐释可以代替社会经验本身。这指向的是一种超验的统一和整全性,凸显的是一种将社会经验文本化、美学化的路径。而这是采用新批评方法的批评者的知识劳动。文学阅读和阐释带来的整全合一的、超验的美学快感与自由民主的公民文化密不可分。批评者成为这种公民文化的培育者和捍卫者。
1966年,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个题为“批评语言与人之科学”的会议上宣读了他的《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一文,这代表着以后结构主义为代表的理论在北美文学文化研究中的兴起,即所谓的“理论时代。”德里达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批判,再加上196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运动,这促成了对于新批评传统下形成的文学传统经典和美感体验的批判。文本美学体验中曾经被浪漫化的“经验的整全性”被“多元性”和“混杂性”的文化政治诉求所取代,曾经为白人男性所独占的文化和社会资本逐步地向女性、后殖民、少数族裔、非主流性活动者等人群开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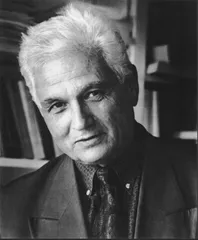
理论在文学文化研究领域的兴起、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议程,与美国冷战后世纪末的多元文化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汇合在一起,这促成了主导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许多年的泛政治化和泛文本化。希斯金和沃纳从这种文学研究中出现的文化研究倾向里面概况出3个特征:一,理论的文本大多来自法国;二,知识工作的泛政治化,这包括女性主义、后殖民等理论的兴起;三,体现在新历史主义研究中的泛文本化(以1983年《表征》杂志的创始为标志):文学经典与各种档案材料并置在一起,后者只是许多种历史和社会文献中的一种,其经典性日益褪去光环(Warner and Siskin, 94-107)。批评考察的对象也从之前单个的文本、作者和意识转换为对“语言结构、欲望或经济资本”的揭示和批判(Love 372)。
以历史长时段的视野来观察20世纪这两种不同的文学文化阐释模式,就会发现它们其实在某些方面具有惊人的连续性。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基督教及其机构性神圣阐释的许多方面逐步转换为人文文化的范畴。更令人吃惊的是,阐释学的“许多人文主义的侧面持续地出现在理应反-或者是后-人文主义的文学研究之中”(Love 372)。在过去几十年以来,人文主义的批评,这包括看起来经典、文本、有机体论、民族、文化、传统以及关于“人”之本身的概念,似乎是一直处于各种理论潮流的攻击之下,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人性等词汇本身似乎就是文化保守主义的象征,是理论化思考单纯和贫瘠的结果,是人文学术研究中过时的词汇和价值观(Love 372)。然而,正如希瑟·洛夫(Heather Love)所指出的,尽管文学阐释的方法和理论变化迅疾,人文主义终结的号角已经被吹了好多遍了,而主要的人文主义价值观在文学研究中仍然是充满活力,它在20世纪前半期和后半期的文学和文化阐释模式中是持续性地存在着的。
20世纪前后两个半世纪的文学和文化阐释模式之间的连贯性还体现在文学文化文本阐释者(批评者)的角色上。澳大利亚学者伊安·亨特(Ian Hunter)从作为教育者的批评者的角度出发,看到文学研究中人文主义伦理观的持续性存在,认为无论是新批评还是取代新批评的理论时代,都存在一个“非常明显的禁欲-教导层面(an intensively ascetic-pedagogical dimension)”(引自 Love 372)。在他看来,教学实践中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是“辨认、认同与纠正、管教的关系,”这是一种形式的人与人关系上的权力管治。他认为在文学批评中存在这种模式,他称之为“教学法上的规则”(pedagogical imperative):(学生 / 读者)观察,(学生 / 读者)辨认、认同,(教师 / 批评者)纠正、管教,(教师 / 批评者)例证、例示。这使得启蒙时代以来世俗现代性语境下的文学阅读和批评成为一个有关道德教育和自我成长的、享有特权的社会场域,这个过程与西方基督教历史上的教牧教导过程是一样的。随着启蒙世俗现代性的进展,以及多元、平等等社会政治话语的展开,德性教育所需要的权威和等级秩序陷于坍塌之中。正是在这种历史社会情形下,伦理价值逐步嵌入到了文学文化文本之中,成为“批评者”这个角色的社会功能所在。结合我们上文谈到的新批评派的文学批评者及文学文化研究泛政治化泛文本化批评者的角色认同、对批评对象和批评工作的态度、与批评研究结果的关系,这里面的确存在一种类似于西方基督教牧师所具有的、由上帝而来的权威感。这种权威感赋予批评者以文化、历史、民族精神、传统等的传承者和身份政治、平等、多元社会价值的创造者这样的角色。
那么,在一个信息文化社会中,人文学的知识日益被信息工业称为文化的内容,而艺术则日益成为多媒体的娱乐,这样的环境下,一般意义上的人文学的未来在哪里?早期以新历史主义方法研究浪漫主义文学的艾伦·刘(Alan Liu)教授在其新书的书稿中提出了“晚期人文批评”的概念(艾伦·刘 41)。人文思想自人类出现以来即存在;人文主义的历史非常悠久,从西方历史上可以追溯至古希腊的文本批评,其在近代的发生发展与宗教的式微和世俗现代性的发生关系密切。正如本文前面所谈,人文学科是随着近代印刷文化的兴起而产生的知识机构化形式(Lauer 133)。这其中的文学批评的形式中,我们还能看到世俗现代性和其之前的宗教教育都具有的教学法上的“辨认、认同与纠正、管教的关系,” 这种关系体现的是由知识、信息及其教导而引起的权力关系。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人文学长期以来所依赖的印刷媒体正在逐渐地与数字媒体相互交织在一起。在今天这个时代里,人文学的基础设施正在急剧地发生着变化,数字媒体时代的文学研究和知识工作与已有的方法之间的连续性和断裂性在哪里?
三、文学研究的社会学转向
在“晚期人文批评”之中,对文学美学层面上的讨论发生了变化,更为强调文学阐释技能和方法,文学批评者之前所拥有的超凡魅力逐步褪去,这引起对作为一个学科的文学研究更为根本的重新思考。比如,约10年前詹姆斯·英格厉什(James English)就认为,“如果我们以历史、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或者哲学学科为规范标准的话,” 过去几十年的文学研究“都太过于文字文学层面了”(引自Love 374)。文学研究出现了许多跨学科的方法,这其中尤其以文学与社会学之间的结合最为明显。希瑟·洛夫称之为“文学的新社会学研究,”她总结出三种类别的文学社会学研究模式:一,对书籍史和其他媒体的研究,这包括文献学、阅读史、书籍流传、版权和知识产权等;二,从经典形成、大学体制和世界文学机制方面对文化价值和文化资本的研究;三、数字人文领域正在发生的比如数据挖掘、可视化等新的阐释模式(Love 373)。洛夫教授做出这些观察虽然已经是几年之前的事情了,但今天大体上依然成立。可以肯定的是,在文学研究发生的社会学转向中,文学文本批评者的角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更多成为文学现象的观察者和描述者,美学意义和政治启示阐释方面的角色功能在消失。
从文学批评史的角度上来看,文学研究与社会学两个学科之间的结合并不是新世纪才有的事情。这最早也许可以追溯到1910年左右匈牙利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卢卡契(Lukács György)那里,他的思想受到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很大的影响(Long 1206)。1970至1980年代中期的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大多数学者都是具有社会学倾向的文学和文化学者。按照詹姆斯·英格厉什的分析,1980至1990年代兴起的一系列后殖民、酷儿理论、新历史主义等批评方法,以及书籍史和新版本目录学都采取了这种“文学社会学”方法的形式。前者谈论的是文学文本生产的社会因素、文本具体形式的社会意义和文本流传与接受的社会效果;后者研究的是文学文本生产和流传所涉及的具体的社会技术机制和物质载体(English vii-ix)。第3种采用了社会学方法的文学批评以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社会文化区隔概念为基础、讨论文学价值和文学经典形成历史和逻辑。
与本文所梳理的长历史时段的文学研究学科史具有很大关联的是第3种文学社会学研究方法之中的一个方面。这方面的研究大致属于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谓的“自反型文学社会学,” 强调对高等教育机构性和学科性的反思,包括其中的课程表、大学教授社会团体、对作为学科史的文学研究重新思考(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与社会整体的关系等),追问文学研究者自身的权威性和研究技能来自于何处(English x)。其中心问题,按照哥伦比亚大学高瑞·维斯瓦纳坦(Gauri Viswanathan)的说法,是一个“教育社会学”的问题,即“认为既有的课程内容并非是绝对的,而是具体的语境中所实现的、建构的情况。” 这种研究对于文学纯粹的美感进行了祛魅,讨论“受教育者和教育者之间的权力关系,文学教育课程内容与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形态之间的关系”(English x)。
对知识生产和教育关系之中权力关系的讨论,以及整个社会媒体人文基础设施环境的变化,加上文学与社会学两个学科都在转向“新的、更为严格意义上的‘描述’或者是‘实用’的方法” (English xii)。这促使作为知识权力结构中本处于特权的、甚至是超验的地位的批评者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事实上,这种变化长时段的历史时期是一直在西方发生着的:由宗教社会中教士阶层之把持教义阐释权(或许再加上西方基督教兴起之前的古希腊罗马社会中的“哲人王”形象),至19世纪启蒙世俗现代性中美学话语的兴起、新批评倡导文化传统及民族精神、至于1960年代的社会政治批评。在这其中,批评者的角色大多都具备传道者、授业者的色彩;在这个过程中,批评者的角色也越来越不再那么超验、越来越凸显其内嵌于社会之中的位置。这是“知识”不断地被机构化生产和流传的过程,是一个知识“民主化“的进程,是批评者的角色不断地被赋予不同的职业形象和技能特征的过程。[1]
知识工作的“职业化”“技能化”和“机构化”尤其体现在近代科学和知识生产的过程中,新的社会知识工作常常伴随着新的问题和新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出现而出现,是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部分。这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许多社会学家研究的对象。比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其写于1904年的《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一文中指出:“不是‘事物’之间‘真实’的关联、而是问题之间概念上的关联定义了不同科学的范围。用一个新的方法解决一个新的问题,这时一门新的‘科学’就出现了”(Weber 68)。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安德鲁·阿伯特教授(Andrew Abbott)在其名著《职业系统:论专业技能的劳动分工》是这样讨论“职业化”是如何维护“文化权威”的:“专家、白领职位朝向一种具体的结构性的、文化的工作管理职位演化。结构性的形式被称为职业,由一系列的机构来组织、管理,使之运转。(职业化的概念,当其最牢固之时,会认为这些机构是按照一定次序建立起来的)从文化方面来说,各种职业通过文化合法性赋予他们的技能以价值,以越来越多地赋予其理性、效率和科学精神的价值”(Abbott 1988: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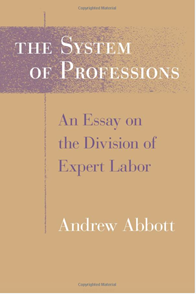
如果以阿伯特教授的“文化权威”和“文化合法性”来观察长历史时段之中作为一种职业的文学文化批评者的话,似乎能看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权威”与“合法性”以不同的形式体现出来。在新批评时代,评论家可以单枪匹马地对文化传统进行整理并以其发言人自居;1960至1970年代,评论家以其生涩的专业词汇建立一系列的批评语言,并引导有关个体身份认同的政治文化讨论;1980年代,其“理性、效率和科学精神”则体现为历史化地讨论一切文化文本,文本之间的等级秩序荡然消失。随着近代印刷文化时代建立起来的“文化权威”感的消失,数字文化媒体带来的文本的便携性和可及性的提高,之前几代批评家职业身份所具有的“可信性”面临新的转换的可能。关于“深度”(民族精神、个体意识、历史精神)的文本解读技能依然是批评家职业身份的必要部分。与此同时,有关“远读”“表层阅读”“描写转向”等阅读和阐释方法的提议也得到了不少的讨论(Best and Marcus 1-21)。在这些新方法中,批评者的角色不再是过去充满英雄主义的伦理感了,而更多是谦逊的分析者和观察者。
四、数字化时代之前的数字人文与20世纪文学批评史
对文学研究科学化、客观化、计量化的尝试是一直存在的,这尤其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近代大学的人文、社会与科学学科的形成密切相关,比如当时文学研究与心理学、统计学等的关系。这里仅举出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关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散文家和批评家弗农·李(Vernon Lee)的共情理论的,这发生于心理学逐渐成长为一门稳固而独立的学科、美学正在被广泛承认为一门学科之际。[2]她将阅读的身体情感感受作为一种具身化审美反应来探讨,借助英国的生理美学研究构建出了自己的艺术理论,认为艺术是一种“有机的物理——精神实验。”芝加哥大学英语系的本杰明·摩根教授(Benjamin Morgan)将李的文学批评语境化,他认为“李的共情阅读挑战了一种我们已接受的历史: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生理美学与后来的文学形式主义尤其是新批评派之间存在着断裂”(Morgan 156)。
在李的美学生理学之中,美学感受成为科学观察的对象,经验性的记录语言成为可以观察和分析的“数据。”在1903年和1904年之间,李发表了一系列可以统称为“文学心理学研究”的文章,提出“一种将词性加以量化的数学式批评实践”“将作者使用的动词、副词和主动分词累加起来,并将累加的结果与名词及形容词的总数进行比较”(Morgan 162)。在通过对德·昆西(De Quincey)、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罗伯特·斯蒂文森(Robert Stevenson)的散文问题量化分析之后[3],李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我看来,我是找到了两类文体:一种大部分时候都在表达行动,例如笛福与斯蒂文森;而在另一种文体中,可以说单纯的存在[……]更为优先” (Morgan 162)。弗农·李的方法涉及对语言从词性角度进行量化,将身体经验作为其阅读理论的中心,所追求的是“一种客观的文学批评实践”(Morgan 164)。摩根教授认为,“李的文学批评延伸了19世纪关于艺术令身体活动的观念,却又提出一种现代的计算分析方法来展示这种活动何以能够发生”(Morgan 162)。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同时具有经验具身与数字抽象特征的文学艺术批评实践,将“可靠的认知普遍性与不可靠的感知个体性”(Morgan 165)结合在了一起。按照尼古拉斯·达姆斯(Nicholas Dames)的说法,这种数目阅读方法的起源可以回溯到19世纪的心理物理学以及维多利亚时代文学批评所使用的生理学语言(Dames 189)。李在1923年发表了她的《对词语的处理,及文学心理学其它方面的研究》一书,比新批评的奠基人瑞恰慈的名著《文学批评原理》还早一年。在这本书里,她曾幻想自己可以“分析足够多的书页——比如说他写过的所有书页[……]从而实现一种对每个被作为比较对象的作者用过的全部词汇的平均分类。‘应用于文学的统计学测试’[……]请允许我推荐那些急切想要成为普通评论者的年轻先生和女士采用这种研究方法”(引自 Mogan 1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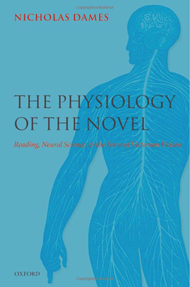
20世纪文学批评史的发生发展就是在弗农·李可以以其“文学心理学研究”统一起来的“可靠的认知普遍性”与“不可靠的感知个体性”之间展开的。在“可靠的认知普遍性”不足的地方,就需要“文化权威”和“文化合法性”来调和维持。如果换一种说法的话,那就是艾伦·刘教授2013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来的数字人文的“意义问题,”即存在于“量化阐释与人为意义上的质化阐释”之间的关系(Igarashi 485)。后者更多是新批评派“细读”的工作。美国学者五十岚洋平(Yohei Igarashi)则从瑞恰慈早期的文学批评实践出发,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谈论“细读,”试图恢复一些新批评派之前的更为强调“量化阐释”与“质化阐释”之间关系的“细读”文学批评实践方法,进而勾勒出一种丽莎·吉特尔曼(Lisa Gitelman)所称之为的“数字人文的前数字化时代历史”(Igarashi 486)。在五十岚洋平看来,瑞恰慈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倡导的“细读”和他所主张的“基本英语”都与当时非文本细读、尤其是统计学里最新的学术研究进展密切相关。五十岚洋平从为今天文学研究者完全遗忘了的、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学生爱德华·桑代克(Edward Thorndike)的教育心理学谈起。桑代克将统计的方法带入了心理学之中,曾在其1904年编撰的教材《精神与社会丈量理论入门》中反复强调“凡是存在的,皆以数量的形式存在”(Igarashi 488)。在他的教育心理学理念中,阅读能力、人类学习的能力都是可以量化的;他从四百万的词汇中,拣选出一万个最为常用的,并将其分为五个语料库——这些包括:“孩子的阅读”“标准文献”“常见事实和行业用语”“报纸阅读”“通信”。
与此同时,英国语言学家C.K.奥格登(C.K. Ogden)与瑞恰慈开始合作写作发表于1923年的《意义的意义》一书。他们发现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事情都可以通过与其他事情的关系来定义,他们总结出来了一些必要的、基本性的关系:相似性、时空关系、因果关系等。通过这个方法,他们发现只需要几百个英语单词即可表达一切意思。这是“基本英语”的萌芽。按照瑞恰慈的定义,“基本英语”的出现是为了两个目的:一,“作为一个国际辅助语言[……]全世界一般交流、商业和科学之中使用的母语之外的第二语言;”二,“提供学会通常英语的理性入门[……]对自然语言为非英语的,以及对说英语的是一本语法入门书,在每个水平的阶段上,鼓励清楚的思想和表达”(Igarashi 492)。这两个目标,即语言的学习能力和交流能力,都受到了桑代克的以统计学为基础的教育心理学的影响(Igarashi 492-493)。奥格登企图系统化英语语言,这与桑代克的提议是相似的。即,这也正是研究“基本英语”的学者们——比如丽塔·雷利和刘禾——对它的定义:“将英语概念化为一个统计系统”(Igarashi 493)。
按照五十岚洋平的研究,这深刻地影响了瑞恰慈。后者出版于1929年的《实用批评》是后来新批评学派的奠基之作。在这本著作中,瑞恰慈在寻找一种类似于“基本英语”的方法,目的是为了能让学生更好地以“意译”的方式来解读诗歌。在其著名的“实用批评”实验中,瑞恰慈常常将诗人的名字、诗歌的题目和历史时代等信息抹去,然后请学生(这其中包括著名诗人和评论家T.S.艾略特)对诗歌进行价值判断和阐释。瑞恰慈看到他学生们针对诗歌做出的评论或者是判断,多是基于诗歌本身或者其形式引起的情感反应,他们却忽略了诗歌的意思,或者他们根本上就忽略了对诗歌意思的阐释。他认为这是扭曲了诗歌的阐释过程,“所有可敬的诗歌都希望得到细读,”这个过程需要“注意诗歌的文字上的意思”, 需要将人为的阐释,“读者个人的情形”搁置起来(Igarashi 495)。通过“意译”的形式完成对诗歌意思的、不扭曲的表达,这并非易事,这也正是“基本英语”对瑞恰慈有用的地方。在《实用批评》之后,瑞恰慈就着手写了几本关于“基本英语”的著作,这包括常被忽略的、《实用批评》的续集《教学基本:东方与西方》(Basic in Teaching: East and West)。他通过自己在剑桥、哈佛、北京清华大学等地教学经验,来证明《实用批评》只能通过“基本英语”的方法来交给英国、美国和中国的学生。只有这样,学生才能避免意译过程中的同义词重复,才能观察到诗歌中的措辞和诗歌中语义模棱两可的地方,只有这样,意译的“工作才是阐释的纯粹意义上的练习”(引自Igarashi 496)。也就是说,瑞恰慈在尽量降低任性的、主观的和情感的阐释趋势,他认为这会扭曲对一首诗歌的分析。而“基本英语”这样的“统计系统”资源正能为其所用:它是一个“有限的媒体,”有有限的字数,同时会限制“错误的联想和情感影响的干预”(Igarashi 496)。五十岚洋平认为,瑞恰慈采用的这个阐释方法所要达成的分析目标与今天数字统计分析的目标是一致的,也就是艾伦·刘所认为的数字人文“白板阐释” 之梦:“在阐释开始的时候,去除、或者至少是关键性地延宕人的观念作用”(Igarashi 496-497)。
刘是在讨论斯坦福大学文学实验室发表的赖安·霍伊泽尔(Ryan Heuser)和朗·勒-凯克(Long Le-Khac)的题为《2958部十九世纪英国小说的量化文学史:语义群的方法》的文章的时候提到数字人文“白板阐释”的。这指的是“以无理论假设的现象的发现开启的阐释过程”(Liu 414)。按照霍伊泽尔和勒-凯克自己的说法,这是指“一种未经指导和管理的方法,没有从数据使用者而来的主体性投入便生成主题”(Liu 415)。也就是说,一台计算机不经阐释者确认某个具体的主题以及从阐释者而来的最初的概念,就可以以算法的方式阅读文本,并且发现导向主题的语义群。作为一个曾经实践新历史主义的文学研究者,刘其实是反对这样的方法的,他说,这指出霍伊泽尔和勒-凯克并没有实践这样的“白板阐释,”相反,他们意识到机器发现的语义群可能为超出人类能理解能阐释的范围。
也就是说,数字和统计的抽象过程并不会带来“白板阐释”的可能性,批评者、阐释者、数据的整理者和使用者这样的“媒介角色”始终是知识生产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也是其所生产的知识的一部分。瑞恰慈希望通过“基本英语”这样的“统计系统”来获得关于诗歌阐释的没有主体情感的透明、简单的意义,这个方案也是这个“白板阐释”的一个版本而已。更为有趣的是,正如五十岚洋平所指出的,在瑞恰慈这里,在文本“细读”这个文学阐释技巧最初的理论化进程里,当时的文本“远读”——即统计分析而来的“基本英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而这种文本细读与远读之间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后来逐步地分流为不同的方法:一方面是自1920年代至今的教育心理学中关于“可读性”问题的研究,另一方面是瑞恰慈统计分析 / 细读结合体随着美国新批评学派的发展而消失了。后者部分缘于布鲁克斯在其《精致的瓮》中所提出的“关于意译的异端邪说”新批评信条。按照这个信条,每首诗里都有一种信息的陈述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布鲁克斯反对将诗歌意译为简单、朴实的“基本英语”可以表达的信息,认为诗歌的意思并不存在于可推断出命题的内容那里。按照约翰·吉尔利(John Guillory)的理解,这是出自于由当时科学发展带来的有关诗歌意义的知识论焦虑。即,坚持认为如果科学事实可以推断出命题的话,那么诗歌里面存在比科学更为真实的“真理,”这部分“真理”是不能简约为能得以证明的科学议题的,而这部分只能通过新批评派别坚持的细读文学批评实践才能获得(Guillory 159-160)。这是一种对于文学阅读和阐释工作之中所包涵的社会和文化资本的建立——即是关于不能验证的“真理”的,是对文学阐释者职业地位“文化权威”和“文化合法性”的捍卫。这就回到了上文勾勒出的20世纪前半期盛行的文学批评模式,及其所创造出的文学批评者的角色。
有关一些有限的文学经典的文本细读,斯坦福大学文学实验室创立者弗兰克·莫雷蒂(Franco Moretti)教授在2000年的一篇讲世界文学的文章中将其指认为“神学性”的文学批评实践,并提出了一种更为“科学的”文学研究“远距离阅读,”即“远读。”远读将大规模的数据库和由数学、生物学而来的抽象的分析模型结合起来,高度依赖量化信息的可视化展示,将文本转化为可供考察的数据,从范围宽泛的地理学和历史系体系中观察文学的变化。[4]对莫雷蒂来讲,距离“是知识产生的条件和情形:它允许你集中在比单个文本大或者是小的分析单位上:文学手法、主题、修辞——或者文类和体系”(Moretti 57)。莫雷蒂承认他是从社会科学——具体来说是经济史研究中的世界体系学派、法国年鉴学派、计量社会学等——那里获得的灵感,他在文章的开始引用了马克斯·韦伯关于社会科学方法的观点。这个关于文学批评实践的概念常常被认为是数字人文文学研究(以及总体上的文学研究)在新世纪再出发的一个标志。而事实上,莫雷蒂自己早在1983年就提出过一种“象征形式的社会学。”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莫雷蒂有关文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只是1960、7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方法论变化(包括书籍史等)中的一种,虽然“远读”的这个用辞是他发明的。除了常常以大范围社会批评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之外,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60年代的学术研究就是在讨论“远读”这种方法的时候不可忽略的“史前史”。的确,“远读”这种方法并不是莫雷蒂教授一人2000年灵光一现的个人独创,而是20世纪(或许更早)文学与文化批评中许多人工作的汇流。[5]比如,威廉斯在1961年发表的《漫长的革命》一书中就已经预示了当前“远读”长历史时段考察文学史的倡议:“没有人真正懂得十九世纪小说;从印刷出版的长部头小说到报纸上刊载的五毛钱连载小说这所有的作品,没有人读过全部,也没有人可能读完全部”(引自Underwood, “A Genealogy”)

莫雷蒂拒绝传统人文研究中“近距离”地考察和阐释文学文本,将文学和文学史看作可以通过数据客观分析得出的变化趋势和模式。这强调了人文研究中的科学权威性、知识的可归纳性、知识生产的透明性,人文研究者的角色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变化,伊安·亨特所指出的无论是新批评还是取代新批评的理论时代之中都具有“非常明显的禁欲-教导层面”的人文主义伦理观逐步褪去了,文学批评者成为冷静、客观的数据和模式变化的分析者。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已有的文学文化阐释技能之外,社会科学、计算科学被介绍到文学研究领域,作为一种职业的文学研究的“文化权威”和“文化合法性”再次得到了确定。这正如莫雷蒂斯坦福大学文学实验室主任一职的继任者马克·阿尔吉—休伊特教授(Mark Algee-Hewitt)所说,以计算的方法来研究文学和文化,“不是要用数学严谨性取代学者们数百年来发展出的阐释技巧的虚拟人文学科。它是增强版的人文学科,在最好的情况下,能展现最仔细的细读读者往往也看不见的新类型的证据和仔细考虑过的理论观点,二者联手产生新的批评研究”。[6]正是“增强版的人文学科”之中所要增加的部分提升了作为职业的文学研究的“文化权威”和“文化合法性”。这也许是在“晚期人文批评”时代突破印刷文化基础设施淡去这样一个背景下作为文学文化研究职业者凸显自身工作之“理性、效率和科学精神的价值”的方法之一。
莫雷蒂的远读、以及以计算和数据为核心的计算文学批评引来了许多的批评。其中之一种来自于人文学研究阵营中对数据抱有天生敌意的文学研究者。比如卡蒂·特林佩娜(Katie Trumpener)就认为,“莫雷蒂以统计方法驱动的文学史研究一个让人困惑的方面是,它似乎使得一只非个人的、隐形之手成为必须的”, “莫雷蒂通过统计解决的问题,也同样地可以使用比较不同的文学体系而解决”(Trumpener 164,169)。[7]对于许多人文主义者来说,这种批评似乎有效。仔细分析会发现这里面存在着一种想要保全一个纯粹的、完全不受历史社会条件影响的人文研究的个人浪漫主义英雄气概。在这种气概中,我们能辨识出存在“非常明显的禁欲-教导层面”的人文主义伦理观。而在这背后,是显而易见的知识和权力的等级秩序。
澳大利亚学者凯瑟琳·博德(Katherine Bode)提供了一个更为有用的批评。在莫雷蒂看来,文学数据是“事实,”以理想的状态独立于阐释。这样的看法一直到2013年都存在于莫雷蒂的学术思考中。博德从文本校勘学的角度出发,认为莫雷蒂忽略了学术研究中有关基础设施的层面。她引用了其他学者的研究[8],认为虽然新批评学派早就终结,然而对于文献学知识的不重视仍然存在于以文本为中心的新批评式的批评修辞中:认为文学作品就是文本,文本和数据是单独的、稳定的、自足的实体;不重视文本和数据记录资料的多重多样性,包括忽略文献学以及学术文献校勘能对文本物质形态历史所做出的贡献。这种对文学体系的有限的、抽象的、甚至是非历史化的处理与其所号称反对的细读其实无异,忽视了文学作品其实是具有自身的社会、经济、机构和技术结构的。博德反对这种对于学术研究材料的抽象和简约,认为“数字化的学术研究材料,就如文献目录一样,是具有阐释性性质的建构,它们依然在变化之中,不仅仅是内容上面,也包括形式上面,在这个过程中为文学史研究提出重要的实践和概念上的挑战”(Bode 82)。文学史的研究要求的并不是新旧方法之类的,而是新的能处理文本记录复杂性(尤其是新出现在数字知识基础设施中的复杂性)的研究目标(Bode 92)。她认为文学体系中的学术校勘研究文本流传过程、文本间的历史和社会关系,并将这些展现为文学史的一个部分。用批评家杰罗姆·麦克盖恩(Jerome McGann)的话来说,学术校勘是“巨大分散网络的一个模型,一个理论的实现[……]我们是在这个网络中表现我们的知识的”(Bode 97)。一个文学文本学术校勘本的内容包括3个部分:历史介绍,描述历史语境、理解历史语境的学科基础、对文本的取舍和编辑原则;校勘机制,这是第1部分的原则如何运用到具体的文本;校勘后的文本。[9]按照博德的说法,“学术校勘后的文学体系数据集并不是作为原始数据。相反,校勘后的文本因为有其相关的‘历史介绍’和‘校勘机制’部分,构成了一个文学历史事件和联系的历史语境模型,是一个介于越来越复杂的数字学科基础设施与文献历史分析之间的阐释媒介物”(Bode 99)。也就是说,从作为文学体系基础设施建设一部分的文本校勘学的视角来看,构建文学数据本身即是一项阐释性和分析性的活动。而莫雷蒂等在号称数字人文可以直接、全面、客观地表现文学研究和文学史时,他们只是使用了文学体系之中非常有限的一部分内容,没有使用包括和构建文学文献文本体系的机构方面和基础设施方面的资源,也因此并不能达到其所宣称的研究目的。
凯瑟琳·博德的这项针对计算文学研究有关抽象化数据、忽视文献基础设施的批评是有效的。作为文学批评方法的新批评派虽然几十年之前就不再处于其高峰期了,“新批评霸权”的幽灵还存在。辨识和批评这种幽灵的途径有许多,其中一条就是从人文基础设施的层面出发,以文学文献为一个体系,在批评的方法和实践层面注意这个体系的各种层面,尤其是文献文本的物质和历史层面。[10]毫无疑问,这明显减弱了评论者的重要性,而使得阐释成为文学文献和体系构建社会历史之中的一个环节。也就是说,阐释的活动始终是文学文献知识网络中的一个进程,并不能提供任何客观的、全面的、科学的、具有权威性质的论点。
上文提及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安德鲁·阿伯特教授,在其最近的一本题为《过程社会学》的著作中提出一种“过程性的方法:”“这种方法假设社会世界中的一切每时每刻都在不断地发展、再发展、恢复原状(以及一些其他的事情)”(Abbott 2016:ix)。具体到我们在这里谈的人文学研究的脉络里面,我们也许可以说,批评和阐释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性”的社会进程。以较长的历史时段来看,批评者和阐释者越来越成为这个“过程性”社会进程的一个部分,而不再是超验于所阐释的材料、所面对的读者观众之外。这体现了一种人文知识“民主化”的过程,是新的人文知识形成机制建立的过程。在我们在此谈及的人文批评发展的脉络中,数字人文及其文献文本基础设施研究是这个进程目前的阶段。在此之中,阐释者本身也是更为明显的文献文本的生产者和建造者,而并不仅仅是批评者和评判者;阐释者更为自觉地凸显阐释知识过程的透明性和过程性,知识的生产、教育和流传愈发成为反思的、建设的和“过程性”的。文学研究的文献化文本化信息化倾向、知识阐释和人文批评的“过程性”进程,这一切意味着绝对精神的褪去和人文权威的消失,这一切都是启蒙世俗现代性之下的知识生产理性化、科学化、职业化、机构化所主导的。
五、中国语境中文学阅读和批评职业化的问题
在中国的语境中来考察的话,首先,“文学”机制本身是随着西方现代性与中国本土历史文化传统的冲撞而产生的。“文”在中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具有非常丰富的政治和社会涵义,“文”的传统是随着中华文明的发生而发展的。按照章太炎先生的看法,“孔子称尧、舜,‘焕乎其有文章,’盖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谓之风;八风从律,百度得数,谓之章。文章者,礼乐之殊矣”( 278)。“文”是整体上的社会文明秩序,也是与野蛮区隔开来的标志。在19世纪以降,作为近代文学基础设施的印刷文化技术随着传教士进入中国,江南机器制造局和格致书院等机构开展了从各种途径流传而来的西方知识的翻译计划,再加上清末的新政以及京师大学堂的建立,这使得中国传统的学术系统面临重构和转化的局面。在1902年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以及1903年由张之洞主持的《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我们看到了作为学科的“文学”的诞生。从“文”到“文学”的过程是中国传统政教秩序瓦解、新的社会秩序形成的过程。章太炎对这一学术现代化过程抱着批判性的态度,他1906年在东京国学讲习会所做的题为《论文学》的演讲中认为,“何以谓文学?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凡文理、文字、文辞,皆谓之文”( 277)。在这里,文学被太炎先生按照其物质载体的形式表现出来,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拓展。最近有学者考证,认为这与1902年发生于太炎思想中的“社会学转向”(史伟 164)也许不无关联。这个问题也许要更为复杂,我们也许可以说,这是“出于他对当时以及不久的将来世界的功能性的理解所做出的,这与现代性规划中将文学作为一个分类的设置截然不同”(陕庆 58)。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现代文学与旧文学的关系、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关系,一直是现代文学学科之中非常复杂的问题。
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大学学科体制中文学研究学科的产生都与启蒙现代性条件下发生的认识论转型有关系。然而,“西方早期浪漫主义属于一种内发性的民族主义,故注重自身传统经典的继承超越,以此作为克服异化与重建生活的手段。而中国的新文学源自一种外源性的民族主义,故强调对自身传统的破旧立新,以此作为救亡图存与抵抗外辱的工具。从而西方用文学拯救的是个人生命的价值,而中国拯救的是集体国族的生存”(于治中 63)。也就是说,20世纪作为学科体制的文学研究在中国的发生发展中最重要的层面并不是其知识论方面的,而是民族救亡图存。这就使得西方近代以来文学研究学科史中所发生的问题、所发展的议程,与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研究的路径和学科发展的议程必然是不一样的。中国的语境中,如何处理文学阅读、文学研究职业化和科学化,这会是一项非常复杂、同时也是非常让人兴奋的挑战。中国文学研究之中数字人文方法的发展,就远不仅仅是面临比如如何处理非字母语言脚本等这样的技术问题这么简单了。可以肯定的是,这必然是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和职业化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问题,也必然需要处理实证研究和中国阐释学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11]
注释:
[1]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到这中间的某种传承性。比如,在20世纪的文学文化批评中,文化研究的学者雷蒙德·威廉斯为利维斯的学生,而以媒体理论闻名的麦克卢汉也曾为利维斯和瑞恰慈的学生。
[2]Vernon Lee,真名为维奥莱特·佩吉特(Violet Paget),1856-1935。
[3]Thomas De Quincey (1785-1859),英国散文家;Daniel Defoe(1660-1731),英国小说家;Robert Stevenson (1850-1894),苏格兰小说家。
[4]事实上,莫雷蒂“远读”的概念最初是作为一种世界文学研究(2000)的范式提出来的,之后有关文学史(2005)以及计算、数字数据、文学理论(2013)等侧面才逐步发展出来。参见Katherine Bode, pp.79-80.
[5]比如,根据雷切尔·布马(Rachel Buurma)和劳拉·赫弗曼(Laura Heffernan)的研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英语系的约瑟芬·迈尔斯教授(Josephine Miles)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在运用这种方法进行有关罗马诗人偏爱的形容词这样的研究了,是远早于莫雷蒂等计算技术研究文学的前驱性角色。参见雷切尔·布马,劳拉·赫弗曼,《查找与替换:约瑟芬·迈尔斯与远距离阅读的起源》。
[6]Mark Algee-Hewitt, “Criticism, Augmented:” https://critinq.wordpress.com/2019/03/31/computational-literary-studies-a-critical-inquiry-online-forum/。这是《批评探索》杂志针对其发表的美国圣母大学笪章难(Nan Z. Da) 教授《以计算的方法反对计算文学研究》(“The Computational Case against Computational Literary Studies,” Critical Inquiry Vol. 45, 2 [2019]: 601-639)一文组织的批评回应文章。笪章难教授的这篇文章以及部分回应文章的中文版刊登于《山东社会科学》杂志2019年第8期由姜文涛、戴安德组织的“数字人文:观其大较”学术专栏中。参见霍伊特·朗、安德鲁·派博等。
[7]在最近的讨论中中,圣母大学笪章难(Nan Z. Da)教授《以计算的方法反对计算文学研究》一文,以基本统计原则从实证层面讨论计算文学研究,认为鉴于语言修辞和阐释的复杂性,计算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和理论前提并不适用于分析文学、文学史和语言学的复杂性。参见笪章难。
[8]这包括William Cain,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New Criticism”. Modern Language Notes 97, 5 (1982): 1100-1120; Jerome McGann, “A Note on the Current State of Humanities Scholarship”. Critical Inquiry Vol. 30, 2 (2004): 409-13; Paul Eggert, “The Book, Scholarly Editing, and the Electronic Edition” in Resourceful Reading: The New Empiricism, eResearch, and Australian Literary Culture, edited by Katherine Bode and Robert Dixon. Sydney: Sydney UP, 2009: 53-69.
[9]关于这方面的实践,可以参见Bonnie Mak, “Archaeology of a Digitization,”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65, 8 (2014): 1515-26。Mak的文章讲的是“早期英语书在线”(Early English Books Online)的文本校勘过程。参见Katherine Bode, p.98.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文献校勘越来越成为学术讨论的热点问题。王风在所编的《废名集》之《前言》部分对现代中国文学作品的校勘有很精彩的见解,与这里Katherine Bode所谈的不谋而合,参见王风,《前言》,《废名集》第一集,王风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17。
[10]“基础设施研究”(Infrastructure Studies)正在成为一个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新的研究领域和方向。文本文献的基础设施包括修道院图书馆、手稿本抄写员以及图书馆博物馆等。参见James Smithies, The Digital Humanities and the Digital Modern 第5章“Towards a Systems Analysis of the Humanities”. Palgrave MacMillan, 2017:113-152. 以及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艾伦·刘所领导的“思辨基础设施研究”(Critical Infrastructure Studies, cistudies.org.)。参见艾伦·刘。
[11]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数字人文方法已经取得了一些学术研究上的进展。参见赵薇。
引用作品:
Abbott, Andrew. The System of Professions: An Essay on the Division of Expert Labor.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 Processual Sociology.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6.
Best, Stephen and Sharon Marcus. “Surface Reading: An Introduction.” Representations Vol. 108, 1 (Fall 2009): 1-21.
Bode, Katherine. “The Equivalence of ‘Close’ and ‘Distant’ Reading; or, Toward a New Object for Data-Rich Literary History.”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Vol 78, 1 (March 2017): 77-106.
Brooks, Cleanth. The Well Wrought Urn. New York: Reynal and Hitchcock, 1947.
雷切尔·布马,劳拉·赫弗曼:“查找与替换:约瑟芬·迈尔斯与远距离阅读的起源”,《山东社会科学》9(2018):45-49。
[Buurma, Rachel and Laura Heffernan. “Search and Replace: Josephine Miles and the Origins of Distant Reading”(cha zhao yu ti huan yue se fen mai er si yu yuan ju li yue du de qi yuan). The Journal of 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9 (2018):45-49.]
笪章难:“以计算的方法反对计算文学研究”,《山东社会科学》8(2019):24-39。
[Da, ZhangNan . “The Computational Case against Computational Literary Studies” (yi ji suan de fang fa fan dui ji suan wen xue yan jiu). The Journal of 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8 (2019): 24-39.]
Dames, Nicholas. The Physiology of the Novel: Reading, Neural Science, and the Form of Victorian Fi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English, James. “Everywhere and Nowhere”.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 41, 2 (Spring 2010): v-xxiii.
Guillory, John. Cultural Capital: The Problem of Literary Canon Form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Igarashi, Yohei. “Statistical Analysis at the Birth of Close Reading,”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46, 3 (Summer 2015): 485- 504.
Klancher, Jon P.. The Making of English Reading Audiences, 1790-1832. Madison, WI: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7.
Lauer, Gerhard.“文化的数字丈量:‘数字人文’下的人文学科”,《澳门理工学报》3(2018):132-139。
[—. “Die Vermessung der Kultur. Geisteswissenschaften als Digital Humanities” (wen hua de shu zi zhang liang shu zi ren wen xia de ren wen xue ke). Journal of Macao Polytechnic Institute. 3 (2018): 132-139.]
艾伦·刘:“通往思辨的基础设施研究,”《山东社会科学》6(2019):40-44。
[Liu, Alan. “Toward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Studies” (tong wang si bian de ji chu she shi yan jiu). The Journal of 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6 (2019): 40-44.]
Long, Hoyt. “The Sociology of Forms,” PMLA Vol. 132, 5 (2017): 1206-1213.
霍伊特·朗、安德鲁·派博等:“推进计算文学研究”,《山东社会科学》8(2019):40-52。
[Long, Hoyt, Andrew Piper, et al. “Promoting Computational Literary Studies” (tui jin ji suan wen xue yan jiu). The Journal of 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8 (2018): 40-52.]
Love, Heather. “Close but not Deep: Literary Ethics and the Descriptive Turn,”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 41, 2 (Spring 2010): 371-391.
Moretti, Franco. “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 New Left Review, January-February 2000: 54-68.
Morgan, Benjamin. “批评的共情:弗农·李的美学及细读的起源”,《澳门理工学报》3(2018):154-168。
[—. “Critical Empathy: Vernon Lee’s Aesthetics and the Origins of Close Reading” (pi ping de gong qing fu nong li de mei xue ji xi du de qi yuan). Journal of Macao Polytechnic Institute. 3 (2018): 154-168.]
陕庆:“章太炎:典籍分类、文类与现代文学,”《文学评论》2(2015):50-59。
[Shan, Qing. “Zhang Taiyan: Classifications of the Canon, Genres and Modern Literature” (zhang tai yan dian ji fen lei wen lei yu xian dai wen xue). Literary Review. 2 (2015): 50-59.]
史伟。“‘社会学转向’与章太炎的‘文学’界定”,《文学评论》4(2019):164-173。
[Shi, Wei. “‘The Sociological Turn’ and Zhang Taiyan’s Definition of ‘Liteature’”(she hui xue zhuan xiang yu zhang tai yan de wen xue jie ding). Literary Review.4 (2019): 164-173.]
Siskin, Clifford. The Work of Writing: Literature and Social Change in Britain, 1700-1830.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9.
Trumpener, Katie. “Paratext and Genre System: A Response to Franco Moretti.” Critical Inquiry Vol. 36, 1 (2009): 159- 71.
Underwood, Ted. “A Genealogy of Distant Reading.” Digital Humanities Quarterly Vol 11, 2 (2017). 19 September 2019: http://www.digitalhumanities.org/dhq/vol/11/2/000317/000317.html.
Warner, William B. and Clifford Siskin. “Stopping Cultural Studies.” Profession (2008): 94-107.
Weber, Max. “Objectivity in Social Science and Social Policy.”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Trans. and ed. by Edward A. Shils and Henry A. Finch. Glencoe, Illinois: The Fress Press, 1949: 49-112.
Wellmon, Chad. “Sacred Reading: From Augustine to the Digital Humanists.” The Hedgehog Review, Fall 2015: 70-84.
于治中:“现代性与‘文学’的诞生——从朱自清与现代文学学科的创建谈起”,《文学评论》3(2019):55-64。
[Yu, Zhizhong. “Modernity and the Emergence of ‘Literature’—On Zhu Ziqing and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Literary Study Discipline” (xian dai xing yu wen xue de dan sheng cong zhu zi qing yu xian dai wen xue xue ke de chuang jian tan qi). Literary Review. 3 (2019): 55-64.]
张瑞卿:“F.R.利维斯与文化研究——从利维斯到霍加特,再到威廉斯”,《文艺理论研究》1(2015):205- 214。
[Zhang, Ruiqing. “F.R. Leavis and Cultural Studies—From Leavis to Hoggart, and to Williams” (li wei si yu wen hua yan jiu cong li wei si dao huo ji ate zai dao wei lian si).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1 (2015): 205-214.]
章太炎:《国故论衡疏证》,庞俊、郭诚永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Zhang, Taiyan. A Philological Study of Classical National Learning (guo gu lun heng shu zheng). Beijing: Zhonghua shuju, 2008.]
赵薇:“‘数字人文’与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计量方法”,《现代中文学刊》1(2019):72-75。
[Zhao, Wei. “Digital Humanities and Computational Methods in Studies of Modern Literature” (shu zi ren wen yu xian dai wen xue yan jiu Zhong de ji liang fang fa).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Studies. 1 (2019): 72-75.]
